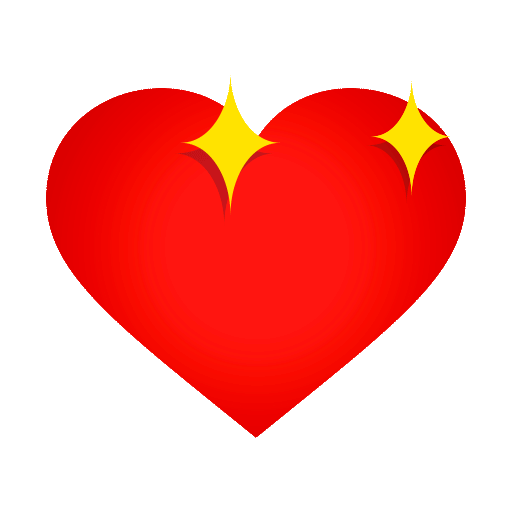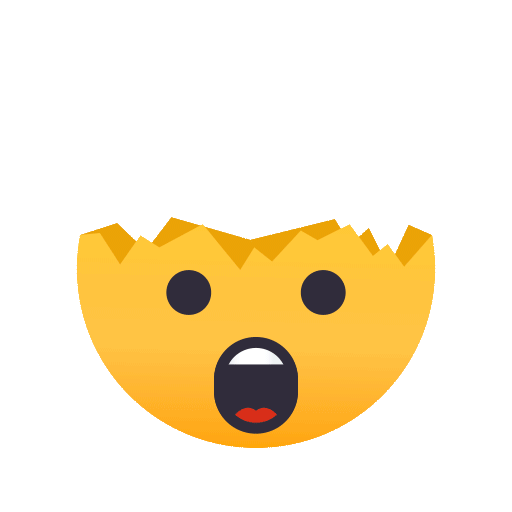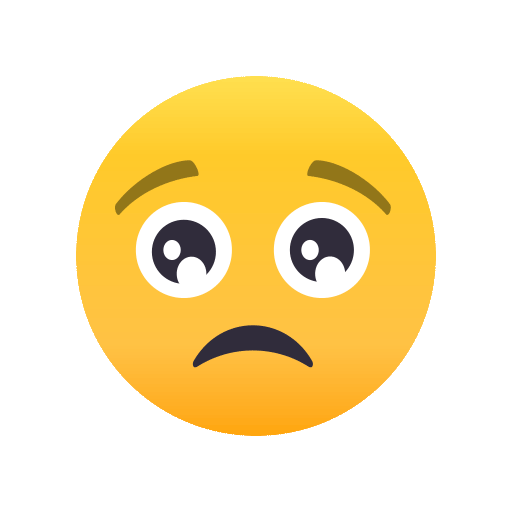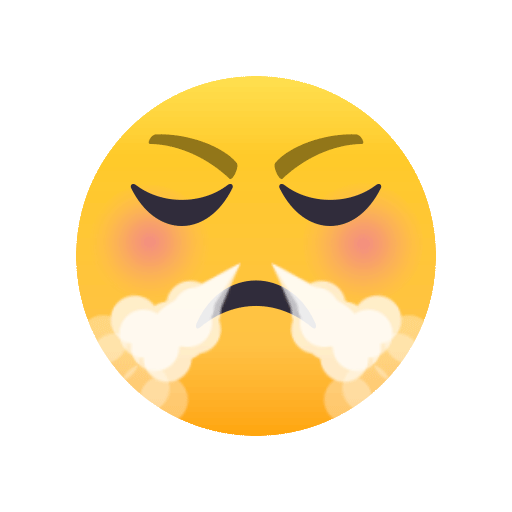人生几回笑脸相逢? 就在刚刚疲倦的一会儿,做了一个梦,梦见我遗忘了一件什么东西,折回去拿,回我奶奶家。 她家住在城区一个破旧的小巷,房屋年久失修,巷子左右的新房都起来了,唯独奶奶家老旧不堪。我放下单车敲打蓝木漆的前门,喊着奶奶,天色已晚,我想她可能已经睡下了。正当我要转身离开的时候,我看到靠近后门的窗户亮起了昏暗的灯。我知道奶奶起来给我开门了。 走到十几年都没有变过的前厅,奶奶问我怎么这么晚来了。我好像已经忘记了所取之物,只是说来看看,一会就走。奶奶走进没有铺上水泥的黑土地厨房,去烧水,说正好洗个脚再走。我感觉屋子里怪怪的,又黑又潮,就让奶奶也洗一下。这回奶奶没有反对,她坐在小椅子上,我帮她倒热水,看到她已经畸形的脚和弓身的后背,心想奶奶怎么样老成这样了! 我有点心酸,便再次和奶奶说,和我们一起住吧,也好一点!奶奶也没有反对我,好像同意了的样子,只是说:"早知道是这样就好了!" 我却在这昏暗的梦中醒来,窗外刮着风,冷飕飕的,今天正是清明十分。 在记忆里,我的奶奶是远近闻名的古怪厉害的角色。从记事起,奶奶就在和我爸爸妈妈吵架,和邻居吵架,和单位职工吵架,没人敢惹她。她怀着强烈的怨念,认为这世上的人都是要害她的。我很小的时候,父母便从奶奶家里搬出来,住在单位的宿舍里,因为怕她吵架。骂人既狠又快,阴晴不定,万事不好琢磨。在家我爷爷不敢顶撞她,在外面熟悉的人更不敢得罪她。 只是我出生的时候,她心情是极好的!六十多岁得孙不易,独子长孙,气也顺了许多。这样的太平日子并没有好长,我母亲还在做月子的时候,她又疑心大起,认为我母亲好吃懒做,就在家里发作起来,一家人不得安身。对我这个大孙子,她极上心,每天都是白天推车逛街,晚上带着睡觉。有一天晚上,我怕黑,要开着灯睡,一关灯就吵闹,奶奶就开始凶我,说我和他们一样,合起来害她。 终于在我大概上小学的时候,父母在单位分到了房子,三口之家独立门户,彻底从奶奶家搬出来。可是这样也没有解决问题,我的童年记忆就是一个强悍的奶奶和爸爸妈妈斗争的过程,爸爸工作的事,妈妈工作的事,爷爷带孙子的事,种种因由,都可以一触即发,也包括我对奶奶态度的事。只要我一耍脾气,奶奶就认为是我爸爸妈妈调唆来气她的,发作一番。 一个厉害的奶奶,却没有让我害怕,因为我知道怎样讨好她!反正小时候的我能说会道,又长的乖巧,也知道奶奶疼我!加上奶奶一直要拉拢我成为她的人对抗我爸妈,我就在这两面三刀中动手脚,一边答应奶奶条件讨糖吃,一边回家还是吵着和妈妈睡。 上小学,就只是我经常去奶奶家吃顿饭,父母比较少去奶奶家了。到三年级,爷爷过逝,奶奶就一个人在小巷的老房子里生活。 爸爸要求我每个周末都去奶奶家玩,也是代他看看奶奶的意思。我把这个要求都当作不得不完成的任务,有时却又迫不及待的想去,因为这回又想买点什么,爸爸不给钱了。 在奶奶家的时间一呆往往一整天,奶奶收集的各种小人书被我看遍,夏天在客厅的门槛上看,吹着风凉快,冬天在天井的砖墙上看,晒着太阳暖和。书看没了就吵着买,买各种好看的书,这也大概是我花奶奶最多的钱。看完了就要奶奶讲些老掉牙的故事,反正在奶奶家并无别的事情可干。于是奶奶就讲些老皇历,说她十几岁和太奶奶在县城开饭店和吃霸王餐的士兵斗争的事,说她在文革中因为被陷害抄家的事,讲她在单位值班被大老鼠咬到手指的事,还有许多讲我爸爸妈妈不好的事,那些三姑六婆要整她的事,就这些书和故事成了我整个童年休闲时光。 后来我长大些了,功课多了,这些童年的书和奇怪的故事也不再吸引我,去奶奶家过一天周末真正成了一件讨厌的作业了。奶奶年纪越大也越发偏执起来,害她的人已经遍布全世界了,包括我。 而父亲在我十三岁的时候突然病逝了,我的父亲,奶奶的独生子! 他们都说通知奶奶来看爸爸,她不肯来,最后来了,也只说了一句"没良心的"。大家都觉得奶奶已经精神失常了。 我没有觉得,每次我再去奶奶家看望她,和她说话的情形和以前并没有差别。 只是要中考了,上高中了,又要高考了,去奶奶家的时间更加少了。 恍惚记得有一次,我在门口叫奶奶,她很久才开门,她说我的声音怎么样都变了。 上高中后奶奶突然中风,幸运的是发现得早。住院后出来并没有严重的半身不遂,只是有些行动不便,多年不往来的母亲似乎头一次出现了。做饭洗衣料理日常,母亲在工作之余去照顾奶奶,太辛苦。我们再三要求她同我们住到一起,方便照顾,她始终不肯,包括当年年底,想让她和我们一起过年,她也始终没有答应。想起来,那时真是凄惨的几个年关。 上了高三,我的日子更不好过。有一个周日的下午我又去看望奶奶,却是大门紧锁,没人答应,我走到后门,趴着卧室窗子看,一片昏暗,看不真切。只好回家。到晚上妈妈告诉我,奶奶已经过逝了。她大概半夜起身,行动不便,绊倒在地,再也没有起来。人在潮湿的地板上早已僵硬,大拇指被老鼠啃掉,只剩了半个。 清理遗物的时候,在我从未上去过的暗阁楼里找到一个老式座钟,那是我奶奶故事里抄家留下的一件器物,他们说这架鎏金的座钟是资产阶级剥削罪证,便把表面的金色全部刮掉了。我看那座钟早已破烂不堪,只好扔掉。 许多年以后,我以为我远离了一身素服的悲痛,远离了那栋幽暗潮湿的小屋。可是梦里常回到那个敲门的地方,那个让人琢磨不定的古怪奶奶,却没有让我害怕。她在那里独自生活了十年,在那里独自腐朽死去。 在城市这个刮风下雨的傍晚,我又回去奶奶的小屋。猛然醒来的时候,记忆的真实只能哽咽无语。